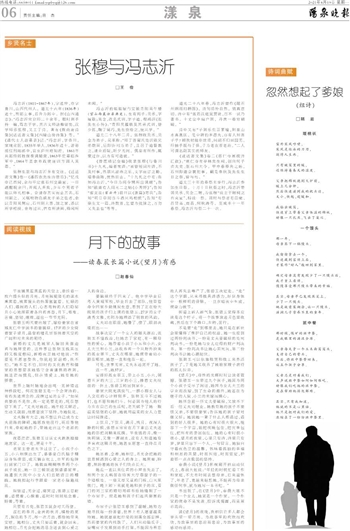平泉镇黑蓝黑蓝的天空上,悬挂着一枚白馒头似的月亮。月亮被褪猪毛的滚水熏蒸着,被蒸馒头的热雾氤氲着。忙碌的人们、嬉闹的人们、心思弯转的人们隐秘且小心地挥霍着各自的喜怨,月下,艰难、苦痛、坚韧、缠绵,溢出一节节光阴。
张碧玉明天要出嫁了,嫁给姜家在省城友仁中学读书的姜毓禄。17岁的少女倚着窗子望月,晶莹的瞳孔里容纳着天空的广阔和对未来的期待。
新婚的丈夫是被家人骗回来强迫着与她拜堂的。这件事让张碧玉极其压抑又极度憋闷,新婚夜里她对他说:“你要是不愿意娶我,你就赶紧退婚,我不怕。”她不是不怕,旧时的文化教育和儒家的思想要求她恪守含蓄谨慎的准则,她迷茫而慌乱,但在情爱上,她有她的骄傲。
世界上随时随地会出现一见钟情这种桥段吧,何况张碧玉是一个会背诗的、有些先进理念的、没缠过足的女子。“如果我娶的不是你,我一定是要走的,现在想留下来了。”丈夫对她说。她年轻又鲜活,生动又靓丽,他愿意放下坚持,为她驻足。
丈夫胸有大志,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丈夫前路的障碍,她愿放他前行,而后等他归来,牵起她的手,带她走出这个老派的家族。
夜幕茫茫,张碧玉目送丈夫跌跌撞撞地离家。这一走,便是十年。
老家主姜老太爷过世了,小叔子小五、小六相继出生了,婆婆姜白氏脑子糊涂身体虚弱,成天躺在炕上,日军的炮弹打到家门口了。她做面糊糊喂养两个小叔子成长,她一日三顿饭送到婆婆屋里,她遭到大院中小女人们丑陋语言的糟践,她挑担起行李跟着一家老小躲避战乱。
烦恼过,无奈过,痛哭过,张碧玉忍耐着,悲愤着,心酸着,还时时刻刻地念着,盼着,等着。
只要有月亮,张碧玉就会对天而望。
涩红的春月,金黄的秋月,橘粉的夏月,铜色的冬月,每一次月出,都给她带来安慰。她相信,丈夫只要活着,就会回来。她相信,月光会把她的思念送去到心爱之人的身边。
姜毓禄终于回来了。他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,毕业后去了部队,他带着命令回家乡做煤炭生意,看到了正在给大院里的孩子们上课的张碧玉。27岁的女子清秀文雅,光阴为她增添了别致的风韵。
丈夫站在眼前,她懵了、傻了,眼泪决堤而出……
战事决定了一个女人的随夫漂泊,张碧玉不懂政治,但她忠于家庭、有一颗母性的爱心,她带着小叔子小五和小六,女儿大兰和小兰,还收养着一个从野外捡来的孤女翠玉,丈夫在哪里,她便带着幼小跟在哪里,她想一直和他在一起。
可是,世事无常,丈夫永远离开了她。
这一年,她37岁。
安排好孤女翠玉,带上小五、小六,领着五岁的大兰、三岁的小兰,捧着丈夫坟前的一抔土,张碧玉转回到家乡。
姜家大院充满戾气,一群小脚女人与人交往的心计特别多,张碧玉斗不过她们,也不愿和她们斗。何必因为他人的行为左右自己的生活呢,老天赋予了她一颗温柔坚强的心脏,她就用温柔的女人力量让时间推进。
上弦月,下弦月,满月,残月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张碧玉常常在月下拿出丈夫送她的那把剑鞘来抚摸。平泉镇的月,像一块明镜,又像一潭湖水,没有人知道她有多喜欢这颗月亮,她甚至愿意一直待在月色之下。
她思着、念着,她相信,月光会把她的哀思倾洒到心爱之人的身上。她熬着,盼着,熬盼着她的孩子们快点长大。
她连一直以来住着的小屋也失去了,和两个女儿蜗居在待客大厅靠窗子的一个墙根处。一扇又厚又重的门板,白天里做门,晚上卸下来就是她和孩子的床,看门的刘三家的媳妇用碎布给她缝制了一个布帘子,便是她和孩子们遮风御寒的墙。
布帘子让张碧玉感到了温暖,她努力地寻找每一份善意,世界上有人愿意温柔待她,她就愿意把经受的刻薄全部忘掉,然而姜家的内核散了,人们从动脑瓜子、耍嘴皮子发展到动手打架,不能因为眷恋故人再失去尊严了,张碧玉决定走。“走”这个字眼,从来都极具诱惑力,好似身体中一根鲜明的骨骼,一旦在暗夜中生成,便奋力拔节。
街道上新人新气象,张碧玉觉得本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将一个故事放进月色里收藏,然后在下个路口,左转,前行。
不是要“走”到哪里去,她只是在新社会里懂得了维护自己的权益。她一生接到过两份判决书,一份是丈夫姜毓禄的处死判决书,一份是她与女儿应得的财产判决书。第一份判决书让她心若死灰,第二份判决书让她心潮起伏。
张碧玉可以依靠租赁和做工来养活孩子了,于是她又收养了被娘家嫂子虐待的孤儿拉弟。
《望月》中,母性的光辉时时让读者震撼。张碧玉一生带过九个孩子,她因为两个小叔子受尽了闲话,她因为女儿大兰的学业而改嫁,到了生命的最终,她还在为继子的入狱、小兰的未嫁而操心。
她怀念前一任丈夫姜毓禄,又放不下后一任丈夫刘继业。她教育她的孩子不要恨父亲,不要恨姜家;告诉她的孩子要对继父好;她说她一辈子什么人都遇过,遇到的好人很多。她的心有时很大很大,能容下一个宇宙,能把夜晚包住,把灾难包住,把所有的委屈包住。她的心有时很小很小,望月的夜里,心里只有诗,诗里只有梦,梦里只容下一个人、一句留言。她独自守着夜色里的温馨,体味着孤独的幸福和相思的苦楚,时而纠结,时而坚定,护着那一点点脆弱的坚持。
春晨小说《望月》影视剧开拍启动仪式上,春晨大姐说:“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家庭,不太有时间去想母亲,后来退休了,年老了,竟越来越想她,不能再为母亲做任何事,就为她写一本书吧。”
书出版了,在《望月》中,春晨大姐不只是一个女儿,她更是一个作家。一个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、控诉或揭露,而是展示高尚。
读《望月》的夜晚,我相信许多人都会举头望一望月亮,为故事里的欢欣而欢欣,为故事里的悲凉而悲凉,为故事里的感动而感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