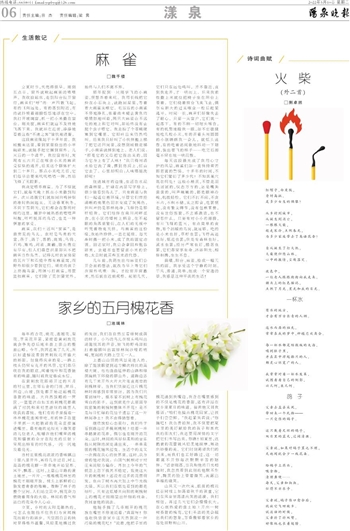立夏时节,天亮得很早。刚到五点半,窗外就响起麻雀的喳喳声。我收拾起床,走到阳台拉开窗帘,麻雀们“呼”的一声四散飞起,有的飞向远处,有的落到附近,有的就扑棱着翅膀悠悠地浮在空中。我打开玻璃窗,抓一把小米撒在窗台。刚关窗,麻雀们就迫不及待地飞落下来。我就站在近前,静静地看着这些“不速之客”愉快地进餐。
这段麻雀缘起于十多年前。我刚搬来这里,看到家里捡出的小半碗碎米,就随手把它搁到窗外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早,我拉窗帘时,发现有五六只正在啄食小米的麻雀受惊似的逃开,后来这个群体扩大到二十多只。那点小米吃光后,它们每早总要来叽叽喳喳一阵,然后飞得了无踪影。
我决定喂养麻雀。为了不惊扰它们,就每天晚上抓点小米撒到阳台。次日清晨它们就如同自鸣钟似的准时热闹起来。无论春夏秋冬,不管下雪阴天,它们都会在黎明时相约这里。睡梦中被熟悉的喳喳声叫醒,听听悦耳的鸟语,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。
麻雀,我们土话叫“家雀”,是最常见的鸟儿。农村是鸟类的天堂,燕子、鸽子、喜鹊、斑鸠、乌鸦、石鸡、雉鸡、河雀、黄鹂、猫头鹰应有尽有,但人们潜意识里却从不把麻雀当作鸟类。记得儿时农家房屋的瓦片下和石缝中都有麻雀窝,而野外却很少看到它们。顽皮的孩子上房掏鸟蛋,用弹弓打麻雀,用笸篮扣麻雀,它们除了更加警觉外,始终与人们不离不弃。
那年捉到一只刚学飞的小麻雀,便想养着来玩。我用长线把它拴在小石块上,就跑回屋里,等着看大麻雀来喂它。毛茸茸的小麻雀不停地挣扎,张着尚未褪去黄色的喙愤怒地叫着,两只大麻雀在不远处的地上和它对叫,却始终没有去捉个虫子喂它。我去拍了个苍蝇硬塞到它嘴里,它却吐出来仍然鸣叫。后来我只好叫了小伙伴搬上梯子把它送回窝里,没想到刚撤走梯子,小麻雀就掉到地上。老人们说:“那是它的父母把它推出来的,因为它身上有了人味!”我只得用清水给它洗了澡,撂到房顶上,任由它去了。心里却明白:人味哪能洗掉呢?
住进城市的边缘,生活在水泥的森林里,忙碌在高层写字楼上,很少能看到鸟儿了。只有麻雀与我们一起适应着环境,尽管它们曾经清晰的亮栗色羽衣变成了灰褐色,但叫声仍是那样纯净,飞得仍是那样轻盈。它们结伴在南川河畔觅食,在小区的矮树上栖息,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繁衍,在人们的无视中听凭着物竞天择。与麻雀的这份缘,我始终珍惜,一直在延续。每天准时撒一把小米,成了我的固定功课。回老家时,我总会拿回些秕谷碎米,去超市也要留意小米的价格,太贵时就买些玉米渣代替。
几年前,我萌生出与麻雀们公开会面的想法,就改为早上等它们在窗外叽喳一阵,才拉帘开窗撒米,然后就在近前观察。起初几天,它们只在远处鸣叫,并不靠近,直到我走开,才一哄而上。后来我索性撒上米就拉把椅子坐在阳台上看着。它们绕着窗台飞来飞去,偶尔有胆大的过来啄食一粒后赶紧逃开。时间一长,麻雀们好像失去了耐心。只要一关窗户,它们就一起落下。有的不顾一切埋头啄食,有的机警地瞪我一眼,却不忘敏捷地吃几粒小米,有的歪着头用圆圆的小眼睛瞧我一会儿,就低头进餐,有的吃着还间歇地抖动一下翅膀,装出要飞的样子……吃完后却毫不留恋地一哄而散。
每天这段晨光成了我用心守护的风景,麻雀们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警惕。十多年的时间,不知它们繁衍了多少代?不知其巢穴筑在何处?这些小精灵,不管是羽毛团团的,仪态万方的,还是嘴角黄黄的,叫声嫩嫩的,都是眼神冷峻,机敏轻松。它们不打不闹,不贪不占,不积不储,来之即食,吃罢便走,没有繁文缛节,没有包袱累赘,没有世俗客套,不去感激谁,也不留恋什么。只要有对小小的翅膀,有片飞翔的蓝天,有点简单的食物,有个温暖的鸟窝,就足够。吃的是小米也好,草籽也罢;飞得高远也好,低近也罢;住处有森林也好,溪水也罢;经历严寒也好,酷暑也罢,它们都安享生命、沐浴阳光、相伴相携,生生不息。
晨曦、阳台、麻雀,绘成一幅天然的画,我享受这个宁静的时刻。平凡、普通、简单,组成一个安逸的景,我感恩这种平淡的生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