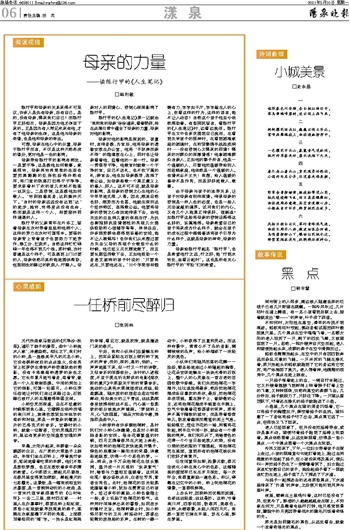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,道尽了游子的凄苦。曲中“小桥流水人家”,诗意盎然。相比之下,我们村的小桥,是一座极其平凡的无名小桥。它没有枫桥夜泊的点点渔火,没有英军上校罗伊在滑铁卢桥悲痛欲绝的剪影,没有卡洛琳廊桥遗梦的余生之愿。它长年累月地弓着身,弯着背,像是一个人在做俯卧操。中间的洞加上它的倒影,可谓一轮圆月。小桥任劳任怨地让村民们走过来踏过去,石板路已被行人的足履磨得珠圆玉润。
小桥空灵而深邃,总在不经意的时候探到我心里。它横跨在低吟浅唱的南川河上,旋律收放犹如宋体字的弯折和衬线,那是一种复杂的螺旋上升的巴洛克式的音乐。安静时的小桥,就像一位智者,它的灵魂是打开的,里边有更多的空间盛放安魂的声音。
早晨,太阳升起来,羊群像一朵朵飘荡的白云,在广袤的大草垫子上游动。羊倌们坐在石桥上,哼着流行音乐,悠闲地看着吃草的羊群。他们不单是放牧梦想,也正在放牧着多年积攒的希望。心中那团火,燃起无尽碧浪,在春风里变得更加硬朗,舞起漫天的七彩霞光。这景致,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,是一首婉转动听的小夜曲,是一首宋代理学家邵康节的《山村咏怀》: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……村里人在办喜事时,都要在桥上贴红纸,那些小红纸就像寻找窝巢的燕子,落脚在农家屋檐下不同的角落,上面都写着相同的“福”字。一抬头是红艳艳的幸福,看见它,就是欢欣,就是撞进门来的春天。
午后,我和小伙伴们总爱躺在桥上,把耳朵紧贴在石板上倾听桥下流水的声音,浅的,深的,高的,低的。一声声地落下来,似一行又一行的诗歌,又似音乐的间奏部分。当时的入迷程度,不亚于现在听北野武的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那段关于雨的背景音乐。流动的山泉将水草梳理成丝成线,轻盈飘逸,随水波的纹理忽左忽右悄然舞动,恰如美女的三千青丝,丝丝柔顺参差披拂却纹丝不乱。内心里一些柔软的部分被流水声铺满。“梦绕桥上月,心飞故园屋。”细品方知曲中意,弹指即是曲中人。
小桥旁种有许多棵泡桐树,是村民们对小桥心存缱绻,也是对小桥孤独身影的安抚。每当花事繁盛的时候,四月正携着春风在大地上奔赴。状如唢呐的泡桐花欢快地亮开嗓子,绿色的底幕掬一捧阳光的笑靥,诗意般地绽放,仿佛一个个彩色的梦。一朵、两朵,当千万朵泡桐花在枝头簇拥,盛开成一片无垠的“东来紫气”时,暗香与力量相互温暖着。这何其壮观!像沙场秋点兵,白者吐芳英,紫者含秀色。此时,泡桐花的目光轻柔地摩挲着小桥,犹如在赞赏自己的孩子。经过多年的熏染,小桥也像隐士一般,身上沾染了泡桐花的香气。这种用时间培养出来的馨香,如同故乡的镇村之宝。泡桐树静止时,如小桥恪尽职守的卫兵;树摇动时,荡漾出轻微的波浪般的乐声。在树的一静一动中,小桥获得了庄重和灵动。而这种布景中,常常少不了鸟的身影,啁啁啾啾的鸟声,给小桥增添了一抹轻灵的亮色。
小伙伴们将随风而落的花瓣一一捡拾,朝圣般地走过小桥隆起的胸骨,让花朵安详地躺在一块块光滑的石板上,整个人的心灵像在一首古老的田园牧歌中穿梭。我们先把泡桐花一字摆开,比比谁捡得最多,然后把泡桐花摆成各自喜欢的形状,最后,把泡桐花串成项链,戴在脖子上,像骄傲的公主,还将泡桐花编成手链套在手腕上,空气中弥漫着花香荡漾的笑声。那笑声不属于精致的城市,而是带着香甜味儿,散发着幽深而潮湿的泥土气息。轻轻嗅它,捏住开花的一端,用嘴将花吹起,两手往中间一挤,就会有一个清脆的响声。我们玩尽兴了,将暗青色的花蒂一个个宝贝般地放入衣袋,没有口袋的把衣服的下摆提起,将泡桐花兜在里面,直到所有的泡桐花被伙伴们收好才肯离开。
任世间繁华如斯,胜景无数,都无法淡化小桥在我心中的色彩,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,每一次怀念,我都重新染一遍色彩。所以,停靠在记忆中的小桥,桥上玩泡桐花的情景,一直都很鲜艳。
上冶头村,因拱桥而优雅而妩媚,也添丝丝轻盈、丝丝曼妙。这桥,守着南川河,四季轮回,散春风,亮春色。这桥,永栖春景,永驻人间四月天。我愿一直把它掬在手里,饮在心里,醉在梦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