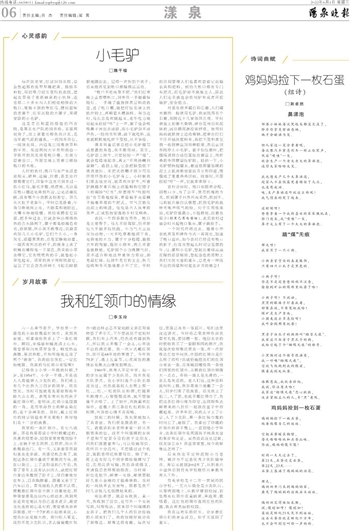每次回老家,经过旧饲养院,总会想起那些张罗犁耧耙盖、修排车补胎、用切草刀切玉茭秸的农民,想起在草房子里抓麻雀的小伙伴,还有那二十多头与人们相依相伴的大牲口:桀骜不驯的枣红马、健壮温顺的老黄牛、壮实沉稳的大骡子、呆萌安静的小毛驴。
这是青石和蓝砖修建的四合院,是第五生产队的饲养场。正面两间房子,顶上盖着亮橙色的洋瓦,是当年最气派的建筑。一间饲养员住,一间放农具。西边是三间堆放草料的平房。东边两间大平房和南边一字排开的灰瓦房是牲口棚。东南方留着出口,外面空地上竖着三根拴牲口的木桩。
儿时的农村,牲口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,耕种、运输、拉磨,甚至出行都需要它们。印象中这里只饲养过一匹小红马,鬃毛齐整,很漂亮。无论是在牲口棚还是牵到外边,总是活蹦乱跳,没有哪个小孩敢去招惹它。那几头大肚子老黄牛,平时总是卧着,牛角匀称地向上弯,大眼柔和地眨巴,大嘴不停地咀嚼。我经常蹲在它面前,把手伸过去,它就会伸出绵绵热热的舌头舔两下。骡子都是棕褐色皮毛,很驯服,但小孩不敢靠近。我最喜欢那几头小毛驴,它们个头小,一身灰毛,眼圈黑黑的,总是安静地站着,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,即使身上落了蚊蝇也懒得甩一下尾巴。我采些小草去喂它,它先嗅嗅我的手,就卷起小草吃起来。顽皮的孩子用树枝抽它,逼急了它会忽然掉转头飞起后蹄狠狠地踢出去。记得一次伤到个孩子,后来他再见到牲口都躲得远远的。
“牲口不吃夜草不肥。”我们经常晚上去看喂牲口。饲养员一手提着保险灯,一手端了盛放拌黑豆料的铁盆,进了牲口棚,就把灯挂在墙上的铁丝钩上,再顺着木槽洒料。每当这时,马儿总是欢跳起来,老牛吃力地站起来轻轻“哞”上一声,骡子也会吸吸鼻子弄出点动静,而小毛驴却不动声色,一脸的无所谓,洒下就吃料,没有就默默地吃碎玉茭秸,从不争抢。
课本和童话里总把小毛驴描写成愚蠢的角色,我不敢苟同。其实,毛驴套上排车,只需轻轻一声“驾”,就会稳稳地起步,真正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。遇到上坡,它会把脑袋低下使劲地拉。车把式的鞭子很少用在任劳任怨的小毛驴身上。小时候我们常去地里玩,就喜欢坐驴车,听着驴蹄踏在青石板上的脆响和它脖子下的铜铃“叮当”,伴着排车“吱扭吱扭”有节奏地摇晃,看着袖手夹着鞭子抽着旱烟的车把式,空气里散发出泥土的味道,处处是大人孩童的笑声,汇成悠扬安逸的乡村交响曲。
农民一年四季都在劳作,牲口是主要帮手。马儿不好驾驭,但并排拉大车能多拉快跑。牛力气大且是反刍动物,一天不吃草都能顶下来,是耕地的主力。骡子十分稳健,能做大车的驾辕,能拉小排车,两头并套也能耕地。毛驴因个小力微脾气好,虽不适合耕地这种重体力劳动,却是最忙碌。拉排车是它的主业,秋天抢收和冬天垫地都少不了它。平时的田间管理人们也喜欢套着它运输农具和肥料。别的大牲口都有专门车把式,而毛驴却不挑拣主人,因此人们走亲戚也会借用驴车或者直接骑驴,安全稳当。
村里有很多碾台和石磨,人们碾米磨面一般使用毛驴。我家院西有个石磨,和附近十几家邻居共用。平时磨盘上扣着大柴锅,磨台是用白灰泥抹的,因日晒雨淋经常掉皮。使用时妈妈就掀掉上边的柴锅,把磨台打扫干净并铺块塑料布,再把玉茭和黄豆倒一些到磨盘顶和磨眼里。然后去饲养院牵头小毛驴,套子钩住磨杆,把缰绳调到合适位置拴在磨盘上,用折叠的布围腰蒙住驴眼,轻拍一下,小毛驴便转起圈来,磨道底那圈坚硬的泥土上就清晰地显出月牙形印迹,慢慢成了重重叠叠凹痕。收面时,只需轻轻“吁”一声,它就乖乖停下。
农村分田时,牲口也跟着分配。因牲口少,为了公平,使用抓阄的方式。抓到骡子自然兴高采烈,抓到牛、马的就只能自认倒霉,抓到毛驴的就唯有唉声叹气的份。对于实用性来说,毛驴价值最小,不能耕地,拉磨也很少(村里已有电磨坊)。此后农村过庙会时兴起牲口集市,骡子最抢手。
一个时代终将过去。随着小型农机普及和耕作方式一再简化,加速了牲口退出。如今农村已经没有牲口的影子。但每当想起儿时司空见惯的牛、马、骡和小毛驴,想起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层层梯田,想起金色的原野上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,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和对逝去岁月的感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