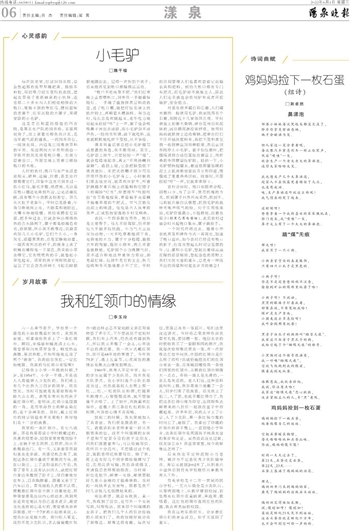六一儿童节前夕,学校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戴着红领巾,来到我面前,郑重地给我系上了一条红领巾。瞬间,幸福感如暖流涌上心头,荣誉感似闪电贯穿全身,顿觉热血沸腾,喜泪盈眶,不知所措地连说了两个“谢谢”。我的脸在发红,一定红如晚霞。我真的与红领巾有缘啊!
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7岁,是1954年。小学一年级,不是说人人都能够入少先队的。我们班上有几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同学,现在想来,当时可能就是先要给那些年龄大点儿的、表现非常出色的孩子戴红领巾吧。老师说,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,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,是十分神圣的。那时,戴上红领巾的同学别提有多光荣啦!我对他们是十二分的羡慕。
我家的一条红领巾,有七八成新,那是我哥哥读小学时候戴过的,我喜欢得要命,回到家常常戴到脖子上,在镜子里左照照、右照照,但从不敢戴着出门。有一天,父亲要带我到阳泉去走亲戚。我感觉机会来了,就把这条红领巾叠成平展展的方块,装在口袋里。上了去阳泉的汽车后,我看了看车上没有认识的人,就把红领巾拿出来戴到了脖子上,很自豪地坐在车上,自我陶醉着。跟着父亲下了汽车以后,看周围的人我都不认得,便戴着红领巾在大街上自豪地走。那种荣誉感是出自内心的追求,我到现在还肯定地认为自己追求进步、渴望当先进的初心是对的。荣誉感夹杂着畏惧感,对一个7岁的小姑娘来说,心理负担还是挺大的。我怕别人看见,说你不是少先队员,怎么偷偷戴红领巾?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跟父亲在阳泉转悠了多半天。下午要返回平定的时候,我们坐上汽车,仍然没有碰到熟人,所以我又多戴了一会儿,心里说不出的满足感。第一次正式戴红领巾,那可是68年前的事情了。今年我75岁了,遇上儿童节,心灵深处的激情还是像火山爆发般喷出。
1960年,我考入平定中学。初一的学生还属于少先队员,而且我是大队委员。在小学时连个小队长都没当过,虽然羡慕别人左臂上那一杠、二杠、三杠的队长标牌,但随着年龄增大,心智慢慢成熟,就不想偷偷干点啥了。上了初中,我既戴着红领巾,还戴上那三条红杠杠的队长标牌,兴奋的心情不言而喻。
到初二的时候,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。我们班是俄语班。有一天,教俄语的李老师拿着一封从苏联寄来的信,说有个叫瑞娜的女孩子想和平定夏令营的孩子交朋友,问我们谁愿意参与,可以给她写信。我听后十分高兴,不想错过这个机会,就跟老师说我要写信。除了我,班上还有好几个同学都给瑞娜写了信,先用汉语写稿,然后译成俄文,再请俄语老师帮助修改。当时邮一封信走航空,邮费一元钱,邮票要贴好几张小金额的才能凑够数。当时的一块钱多么宝贵呀,那都是我平时几分钱几毛钱攒起来的。
寄出希望,就会有收获。某一天,我收到了回信,是另外一个女孩写的,叫斯维达。原来那个叫瑞娜的女孩子,把我们几个人的信分给她的小朋友们了,我的信刚好被分给了斯维达。斯维达很有趣,每次写信,里面总夹有一张画片。咱们这里没这讲究,当时杨乙荣老师告诉我要有礼貌,要回赠一张。他回北京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套颐和园的照片,我就每次给斯维达寄去一张。有一次斯维达在信中问我,中国的红领巾是什么样子的呀?我就给她把我们的红领巾寄去一条。后来她回赠给我一条他们国家的红领巾。苏联的红领巾稍微大一点点,布料一面儿是光滑的,一面儿是发涩的。老人们说,这种面料就叫织工缎。我非常高兴地戴了一会儿,同学们看了很羡慕。后来我上了初二,入了团,也就不戴红领巾了。我把这条红领巾视为珍宝,连同斯维达邮寄来的八封信一起放在盒子中珍藏起来。许多年后,我的儿子上了小学,入了少先队,第一条红领巾戴的时间长了,磨损了。我拿出了珍藏的红领巾给孩子戴上,一直到他小学毕业。这条红领巾是两国孩子纯真友谊的象征和见证,虽然彼此没见过面,但友谊长存!我还常常想,如今的斯维达怎样了?
后来我在平定师范附小当老师,被评为平定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。再后来就到2002年了,从阳泉六中退休后到育英学校继续从事教书育人工作。
育英学校是十二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。一至六年级全是少先队员,从黎明到晚上,从教学楼到校园,到处都有红领巾在雀跃着、奔跑着、歌唱着。这红色的领巾连同红色的队旗,装点着美丽的校园。
我在这欢乐的时节,分享着红领巾们的青春活力,似乎又返回了童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