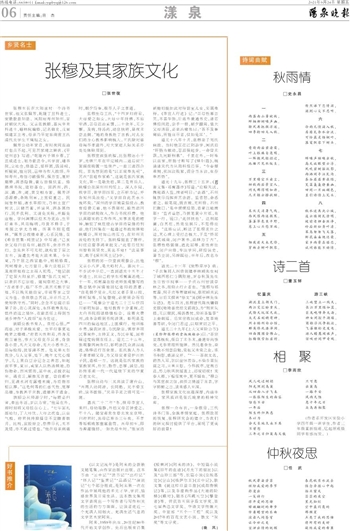张穆生长在大阳泉村一个诗书世家。祖父张佩芳,乾隆丁丑科进士,安徽歙县知县、凤阳府寿州知州,晋封朝仪大夫。父亲张敦颐,嘉庆辛未科进士,翰林院编修,记名御史,戊寅福建正主考。母亲乃平定东南营王氏清代太学生王绳祖之女。
佩芳公幼年家贫,有时夜间连油灯也点不起,可见其家境之窘状。《平定州志》写道:“乾隆丙子领乡荐,丁丑成进士。初为歙县令,兴学宫,建书院,立社仓,修邑志,惩奸匿,毁淫祠,析疑狱,恤穷民,邑绅为作入政颂。升知寿州,寿俗刁敝强悍。佩芳至,厘奸剔弊,洞悉隐微,豪右皆慑伏重。修循理书院,建裕备仓。调泗州,泗、滨、濉、淮、湖、黄交相为害。佩芳详悉源委,条陈利害,上宪倚重之。民间惟种稻,薄水旱即灾,乃相土宜广树艺,以储其蓄,并请风、泗各属仿行,民多获利。又请免关税,并豁免虚粮。学问渊博以经术为吏治,生平好蓄书,风雨晦明,丹黄不释手,于考据之学尤为精,所著书别见儒林。”佩芳公政绩卓著,心系民情。在《希音堂集·祠堂记》中写道:“己亥余父母归自寿州,越四年,余亦终养归。念先世不可无祀,欲构室于居之左右,旋遭先考妣大故未果。今年夏,乃于居之西家塾中,稍稍修葺,列树增舍,七月望日,奉六世祖以下及高曾祖祢之主而入祀焉。”他记叙了定居大阳泉后,修建“张氏支祠”,以表识不忘宗祖,建祠祭祀之大事。“古者孝子,临尸不怍,求其无惭于宗祖,不以贱无能自安,非徒荐享之空文为也。余故敬击其说,并示后之人使知恪守焉。”同时,念念不忘提示后辈子孙,在心灵深处,永怀敬尊先祖、慎终追远之情怀。在歙县任上得到当地乡绅作“入政颂”是为佐证。
敦颐公教书育人,责任心强,严而慈,对子弟极关爱。生平行事更是晚辈之楷模:“府君天性和易,终身无疾言遽色,事大父母克尽其孝,身尝备小册,凡大父母命,无大小悉书之,后每检阅,犹零涕不置。处兄弟无尔我分,与人交事,处下。晚年尤究心理学,几上黑白豆分记念之善恶,如赵叔平事。夏日,戒家人以热汤倾地,恐伤物命。烈风雷雨,虽中夜,必披衣起坐。遇贫乏,解推无吝意。尝自都中归,见清水河有露殣未掩,为质物市棺以葬。”这是何等的仁慈天性、宽厚品德,身教甚于言教,遗德甚于遗金。
敦颐公从师游学时,“每腊必归省,春出冬返,岁以为常。”他虽在外,却时刻将父母挂在心上。“七年罢礼部始归,丁大母忧。大母之疾也,以患气瘕。府君扶持抑搔目不交睫者数月。比殁,哀毁骨立,祭葬尽礼,无不及情,亦不敢过情也。”他在母亲病痛时,朝夕侍奉,极尽人子之孝道。
张穆生母王氏,“十四岁归府君,大母爱之如女,大母中年持佛,不茹荤酒,吾母洁治素馔,二十余年,无少懈。及病,侍汤药,动息扶将,昼夜未尝去侧。”她的身教胜于言教,对儿女们的身心教养影响极大。王氏除对婆母竭尽孝道外,对大家庭人际关系亦处处体贴周到。
张穆堂叔张映櫺,比张穆还小十岁,光绪三年在平定城内二道后街三面阁前购置一处房产,一座三进四合院。首先想到的是“以正寝奉先祠”,其次“前庭作家塾”。这就是张氏家族文化,第一是敬先祖,第二是育后人。映櫺公在深州州判任上,深入乡间,核学田,查学田四至,立石桩为记。并告知州吴汝纶:“义学田自此其永不废坏矣。”深州的学田被豪强侵占,教育经费无着,他不畏强权,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,作为书院经费。他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、实事求是的精神,触犯了疯狂侵占学田的豪强的利益,他们纠集在一起通过布政使弹劾映櫺公,面对如山的压力,在知州吴汝纶的支持下,张映櫺挺直了腰杆。时任总督李鸿章批文:“此君历任知州皆称其贤矣,其名不劾!”这是事实,载于《深州风土记》中。
张穆的另一位堂叔观藜公,比他父亲小八岁,是大峪村人。嘉庆十二年乡试中举后,一直到道光十五年才中进士。比自己的学生祁寯藻还晚二十一年。祁寯藻在给老师张观藜写的墓志铭中深情地回忆老师的恩惠:“自是朝夕受业,凡经义者手录口授,辨析疑难,反复譬晓,必使领会而后已……”观藜公于道光二十三年任四川彰明知县,他对教育十分重视,在太白书院捐银修缮校舍,设膏火费用,政务余暇到书院讲课。彰明县是四川的偏远地区,土匪横行。他训练乡勇,擒获匪首,为民除患。慎审多项民事案件,主持正义,为民申冤,因劳碌过度病倒在任上。道光二十五年,张观藜因病告归,彰明县民众涕泪涟涟,络绎送行百余里。张氏族人为人子者孝顺父母,为父母官者爱护百姓子民,造福一方。这就是张氏家族的家教家风,朴实、勤劳、忠厚、诚信,祖孙传承着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华夏古老文化。
张穆自幼与三兄共读于蒲台山。“吾两人幼同游,长同塾,兄丰姿玉映,读书敏悟。”兄弟手足之情可见一斑。
嘉庆二十二年“冬,继母李宜人来归。母幼端静,外祖父母甚钟爱之。年十八,随宝斋先生眷北发至京师。归府君时,先母已弃养三年矣。不孝等垢裾败絮壅塞盈笥。吾母初至,即为澣濯缝纫,一如先母生时。”张家的新媳妇能如此对待前室儿女,实属难得。《李宜人行述》记:“吾母性寡言笑,不喜华饰,针黹外兼通书史,诸若佛经闺范,尝手一册,朝夕翻阅。值大父母讳辰,必亲治楮帛曰:‘吾不及事舅姑,所能自尽者,仅如是耳’。”
道光十八年十月,张穆妻子刘氏病故。当时他正在江阴游学,闻讯后“肝肠为摧动,忍泪强起步。一命曾未霑,九死断相慕”。千里在外,一时难以返家,肝肠寸断写了《悼妇篇》,婉请诸兄代为从简料理后事。“今春颇乖恻,夜深泣败絮,谓分当永诀,生存难再悟”。
道光十九年,张穆三十五岁。《 斋文集·祁寯藻序》写道:“应顺天试,携瓶酒入监,搜者呵曰:‘去酒’,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。监者怒,命悉索之。破笔砚,毁衣被,无所得。石州扪腹曰:‘是中便便经笥,若辈岂能搜耶?’监者益怒,乃摭笔囊中片纸,有字一行,谩曰:‘此怀挟也’。送刑部谳,白其枉,然竟坐摈斥,不复得应试。”这场应试,断送了张穆求仕之途,其心理上受打击极大,于是“侨居宣武城南,闭户著书,益肆力于古”。张穆性格倔强,遭此屈辱,索性弃仕途,闭户自修,专注学问,研经读史,著书立说,另辟蹊径。半年后,改名为“穆”。
道光二十三年《使黔草序》载:“子贞集同人纠资创建亭林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隅隙地,岁春秋及先生生日皆举祠事……子贞石州皆读亭林之书,而仰止行止者也。”张穆与祁寯藻、何子贞等筹建顾祠,祭祀顾炎武等。日后又撰著“祭文”及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。是年四月,张穆曾代陈庆镛御史撰《劾琦善奕经文蔚疏》,为“刑赏失措,无以服民,竭沥愚忱,仰祈圣鉴事”上奏朝廷。后宣宗收回成命,复革琦善等职,令闭门思过,以昭赏罚之平。
道光二十九年《上大父星阶公书》(星阶即张穆的堂叔映櫺公)曰:“吾宗衰落极矣,侄自丁未冬末,叠遭骨肉惨变,尤非常理所能堪。然忧患余生,益不敢不刻意自勉,竟祖父未竟之业。承书相慰,感涕交并。”“……吾叔文名,蔚然入耳,加以虚怀若谷,不染乡里狂诞之习,且喜且慰。今科拔萃,定膺首选,努力秋风扶摇直上,切祝切祝!来春入都,下榻侄寓中,更不疑也。”穆公与其堂叔之信,叔侄之情溢于言表,字字肺腑之言,读来感人至深。
张穆家族文化底蕴深厚,内涵丰盈,家风族训是张氏晚辈的精神宝库。
张穆一介布衣,一身傲骨,三代诗书门第,全族孝悌家庭。张穆故居的恢复、张穆研究会的建立,为我们的研究探讨提供了平台,展现了更美好的前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