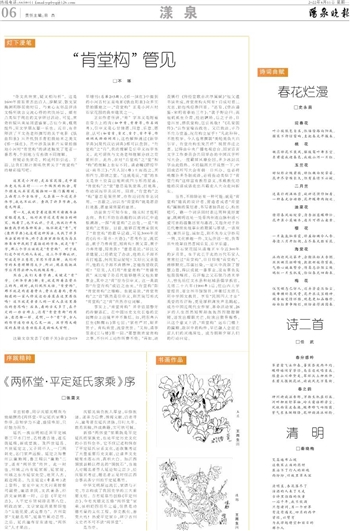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。这是1600年前东晋杰出诗人、辞赋家、散文家陶渊明移居南村后,与素心友邻品评诗文畅所欲言交流心得的欢快场景,颇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文学研讨活动。可见,赏奇析疑从来是同道盛宴,古往今来,概莫能外,实文学朋友圈一乐也。近日,有幸拜读了王文尧老师撰写的关于电影《铁血阳泉》从开机到杀青拍摄始末之美文《那一抹红》,其中涉及该影片实景拍摄地小河村“肯堂构”的讲述触发了笔者一番思考,个别地方有些微不同理解。
析疑必先赏奇,转述何如引述。下面,让我们原汁原味欣赏关于“肯堂构”的精彩描写吧:
这里是小河村,是石家花园,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……一个偶然的机会,有个朋友从石家花园拍回一张门匾雕刻,上面有三个古体字,尤其第一个还是异体字,我也不认识。查找了许多字典,也毫无所获。
有一天,我就拿着这张照片请教书法家银苟先生,他对汉字还是有相当的研究。他看了,也不认识。于是,他就打开电脑查找字的各种写法。他怀疑是“肯”,可《康熙字典》也没有这种写法。又找了许多书法家的字体,终于在唐寅唐伯虎与马王堆帛书中找到了最接近的字体,就是“肯”字,那三个字应该就是“肯堂构”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,这三个字都认识,可这是什么意思,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们对字的本意理解得太少,所以,现在能把汉字应用得出神入化就极其难。
然后,我们又查字典,关键是“肯”字。《新华字典》解:肯,就是附着在骨头上的肉。顿时,我们恍然大悟。“肯堂构”,那不就是肉连着骨头,骨头连着肉,骨肉相连的一家人修筑这些房屋在这里居住吗?这不就是亲亲儿的一家人在这里居住的意思吗?后来,看的古文多了,在平定的一些古碑上,还有“肯堂肯构”的用法,意思都一样。是啊,一个“肯”字,古人的炼字造句功夫已见一斑,汉字博大精深的表情达意功能真是韵味无穷啊。
这篇文章发表于《娘子关》杂志2019年增刊(总第203期),《那一抹红》中提到的小河古村正是电影《铁血阳泉》众多实景拍摄地之一,“肯堂构”正是小河古村石家花园的典型建筑之一。
正如作者所讲,“肯”字本义是附着在骨头上的肉(如中肯、肯綮等,作名词用),引申义是心甘情愿、同意、乐意、愿意、认可(如首肯、肯定、肯于、肯干等,作动词或助动词用),这些解释通过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都可以查到。“肯堂构”之“肯”,我的理解是引申义而非本义,此可谓我与文尧老师理解分歧之肯綮所在。此外,在对“肯堂构”之“堂”和“构”的理解上也有不同。清俞樾《群经平议·尚书三》:“古人封(堆)土而高之,其形四方,即谓之堂。”这就是说,“堂”的本义是夯土使高出地面成四方形的屋基,“肯堂构”之“堂”意思是筑堂基、打地基,作动词而非名词用。同理,“肯堂构”之“构”意思是架房屋,亦作动词而非名词用。一言蔽之,窃以为“肯堂构”就是愿意打地基、愿意架房屋的意思。
访前世方可知今生,晓来时才能明去向。我们不妨在浩瀚的汉语词汇中追根溯源,一探“肯堂构”之出处,一觅“肯堂构”之芳踪。目前,能够百度搜索到关于“肯堂构”的最早记载,可见3000年前的《尚书·周书·大诰》:“若考作室,既厎法,厥子乃弗肯堂,矧肯构?厥父菑,厥子乃弗肯播,矧肯获?”意思是说:“好比父亲建屋,已经确定了办法,他的儿子却不肯打地基,何况架房屋呢?又好比父亲垦田,他的儿子却不肯播种,怎能指望收获呢?”后来,人们用“肯堂肯构”“肯播肯获”来比喻子孙后代能够继承父祖先辈事业,其中之“肯”皆为引申义。这一典故即“肯堂肯构”成语之由来,“肯堂构”即“肯堂肯构”之缩略。也就是说,“肯堂肯构”之“肯”既然是引申义,则其简写形式“肯堂构”之“肯”自然亦应同解。
事实上,“肯堂肯构”并非佶屈聱牙的冷僻语汇,在中国历史文化长卷的宏阔舞台上出镜率并不算低。如,明东鲁古狂生《醉醒石》第七回:“家有严君,斯多贤子。肯构肯堂,流誉奕世。”又如,清李笠翁《三与楼》第一回:“要想做肯堂肯构之事,不怕兴工动作所费不赀。”再如,清查慎行《传经堂歌卓次厚属赋》“祖父遗书读未成,肯堂肯构夫何有?诗成对君三太息,独抱残经莽回首。”还有,《资治通鉴·宋明帝泰始三年》:“裴子野论曰:高祖虮虱生介胄,经启疆场,后之子孙,日蹙百里,播获堂构,岂云易哉!”《孔安国传》:“以作室喻治政也。父已致法,子乃不肯为堂基,况肯构立屋乎?”凡此种种,不胜枚举。今人也常撰联“美轮美奂大启尔宇,肯堂肯构长发其祥”祝贺乔迁之喜。记得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,一度霸屏风靡全国,多少冰封汉字由此焐热。不妨脑洞大开设想一下,中国成语听写大会有朝一日兴办,也必将唤醒许多冬眠成语,必将推动类似于“肯堂肯构”这样富有教育意义、承载教化功能的汉语成语走出古籍走入大众走向新生。
当然,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:就是“肯堂构”建筑的设计者、营造者或者“肯堂构”匾额的策划者、书写者独具匠心、构思精巧,藉一个词语同时表达两种美好寓意,既阐明这是一处骨肉相连血脉相通可爱可亲的温馨居室与港湾,又饱含对子孙后代赓续先祖事业的期冀与厚望,一语双关、兼容并包。诚如是,则不失为文字妙用一例、文化雅趣一件、文坛佳话一桩,我等后生晚辈自然喜闻乐见、乐享乐道。
在石家花园从清雍正至今近300年的岁月里,生于此长于此的历代石家人常常经过“肯堂构”,日日仰视“肯堂构”,潜移默化,耳濡目染,一定从中汲取了智慧力量,得以成就一番事业,没有辜负先祖殷殷嘱托。石评梅之父石铭乃清末举人,曾先后任文水县和赵城县儒学教官,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后,任山西大学管理员、省立图书馆馆员,并兼任太原几所中学国文教员。享有“民国四大才女”美誉的石评梅,更是厚积薄发声名鹊起,成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、革命活动家,26岁的人生虽然短暂却轰轰烈烈铿铿锵锵,迸发出耀眼光芒,绽放出傲骨梅香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肯堂构”远非门楣上的匾额、故居中的构件,早已融入念兹在兹人们的灵魂深处,成为朝斯夕斯人们的行动自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