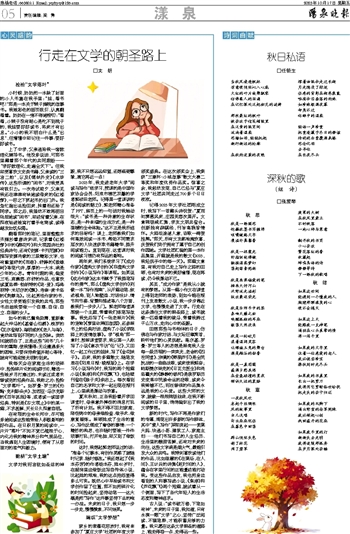捡拾“文学落叶”
小时候,奶奶把一本缺了封面的小人书塞在我手里:“娃,看书吧!”那是一本关于猴子摘桃的故事书。我被彩色的画页吸引,认真翻看着。奶奶在一旁不停地唠叨:“看看,小猴子没有耐心是吃不到桃子的,我娃要好好读书,将来才有出息。”小小的我不明白什么是“出息”,但懵懂中却记住一件事:要好好读书。
上了中学,父亲递给我一套数理化辅导书。他没多说话,可那书里藏着那个年代的共同期盼——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全天下”。但我却更喜欢文史类书籍,父亲读的“三言二拍”,以及《儒林外史》《水浒传》,这些所谓的“闲书”,对我更具有吸引力。一次考试前夕,父亲见我还在津津有味地读借来的《红楼梦》,一怒之下抓起书扔出门外。我急忙跑出去捡回来,抹着泪还给了同学。那之后,我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读“闲书”,却总背着父亲,在深夜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筒读,读得越发如饥似渴。
翻看那时的笔记,里面整整齐齐摘抄着唐诗宋词,记录着《红楼梦》中的《葬花吟》和大观园诗社的经典诗句,还有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描写安娜肖像的三段精彩文字,也有戴望舒的《雨巷》、舒婷的《致橡树》等现代诗,厚厚的一大本,满是少年的心思。青年时期的我,偏爱三毛、席慕蓉、亦舒的作品,也喜欢读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、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《飘》、考琳·麦卡洛的《荆棘鸟》。比起男性作家的书,女性文学更能引发我的共鸣,那些书启迪我要做一个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的女人。
如今的我已鬓角染霜,重新拿起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竟然体悟到不同的人生况味。突然间就明白了,正是这些“闲书”几十年的熏陶,使我懂得: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,只要保持希望并耐心等待,就有可能迎接光明的到来。
我每天会在家庭生活的琐碎中,捡拾碎片化的阅读时间,精选一些被岁月打磨过的、未读过或者未曾读完的经典作品,我称之为:捡拾“文学落叶”。如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等,或者读一读国学经典,特别是《古文观止》中的某一篇,不求甚解,天长日久深意自明。
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,尽可能多地阅读这些能带给人积极影响的好作品。在日积月累的阅读中,一片片“落叶”不知不觉已植根于心,内化为我的精神养分和气质品位,当我遇到人生困境时,便有了从容面对的底气和毅力。
勤耕“文学土壤”
文学对我而言犹如圣洁的神殿,我不只想远远仰望,还想砥砺攀缘,离它再近一点!
2023年,我走进老年大学“阅读与写作”班学习,授课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阳泉市德艺双馨的学者郭祯田老师。记得第一堂课讲的是《阅读的魅力》,郭老师精心准备了PPT,扉页上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:“读书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;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;是一种温暖的生命体验。”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吗?课上,老师教我们如何高效阅读一本书,帮助不同需求层次的人快速获取书籍精华,提升阅读能力。直到现在,这堂课对我的阅读习惯仍有深远的影响。
两年来,我们系统学习了《成为作家》《虚构文学创作》《非虚构文学创作》《小说写作》等课程。如果说《成为作家》这本书赋予了我提笔写作的勇气,那么《虚构文学创作》则像一本“写作指南”,从开篇动笔、叙述视角,到人物塑造、对话设计、情节和节奏、背景和描述等八个方面,教我们一步步入门。郭老师每堂课围绕一个主题,带着我们练笔写故事。我先后写了《一张老照片》《我的宠物》《梦里依稀回故园》,还参照书上的经典对话,虚构了小说《学院路上的爱情故事》。学“视角”那一章时,按照课堂要求,我以第一人称写了小说《寒衣节访“仙”记》,又回忆一起工作过的姐妹,写了《金花妹子》。后来,我的多篇散文、随笔发表在《阳泉日报·晚报版》上。在学习《小说写作》时,我写的两个短篇小说《焦虑》和《芦花飘飞》,也陆续刊登在《娘子关》杂志上。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文字一起出现在报刊上,心里满是激动与欢喜。
夏末秋初,正当我盼着开学回课堂时,母亲意外摔伤的消息打乱了所有计划。我不得不回归家庭,陪伤病中的母亲做检查、做手术、做康复锻炼。照顾她成了生活的重心,写作反倒成了奢侈的事情:一个精妙的构思,也许随时要被一件件琐事打乱;打开电脑,却又到了做饭的时间。
这时,我想起郭老师说过的话:“准备个记事本,有创作灵感了就随时记录、随时修改。”我还想起了《我本芬芳》的作者杨本芬,她60岁时,在厨房里边做饭边写自传体小说,比起她的艰难,我的这点抱怨显得多么可笑。既然心中早给读书和文学创作留了位置,那不如把碎片化的时间捡起来,坚持动笔——这大概是把“写作”这件事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。未来的日子,我只想一步一步走,慢慢摸索,不问结果。
编织“文学梦想”
家乡的紫薇花怒放时,我有幸参加了“夏庄文学”社团的年度文学颁奖盛典。在这次颁奖会上,我荣获“三康杯·小城故事”散文大赛二等奖和年度优秀作品奖。惊喜之余,我忽然发现,自己已经与“夏庄文学”社团共同走过700多个日日夜夜。
记得2023年文学社团刚成立时,我写下一首藏头诗祝贺:“夏雨初霁惠风来,庄园芙蓉次第开。文章锦绣咸汇集,学友文朋共登台。创新独有辟蹊径,刊旨高雅皆情怀。大路坦途遂人意,吉歌一阕贺挂牌。”那天,所有文友都难掩欢喜,庆贺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园地。文学社团汇编的第一本作品集里,开篇就是我的散文《2023,我轻抚手中的每一天》。那篇文章里,有我对自己走上写作之路的回顾,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现在再读,仍令我激动不已。
其实,“成为作家”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。从第一篇小作文在课堂上得到老师的表扬,到如今能在报刊上发表散文、小说,我一步步靠近文学,也慢慢走进了文学。行走在这条通往文学的朝圣路上,读书就像一匹载着我的骏马,带着我跨过千山万水,走向心中的圣殿。
回想那些与书相伴的日子,仿佛在与作家对话、与文坛巨擘聚首,聆听他们的心灵抚慰。高尔基、罗曼·罗兰等人的思想是照亮我人生每一段历程的一束束光,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、宗璞的《野葫芦引》是全民抗战的一曲曲战歌,读来使我振奋;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和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俄罗斯历史变革中民族命运的悲歌,读来令我唏嘘不已;而汪曾祺的作品集永远是我的心头爱。这些大师的文字,就像一根根锦绣丝线,在我不断阅读的日子里,悄悄编织出了我的文学梦想。
新的时代,写作不再是作家们的专属,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群体,其中“素人写作”异军突起——卖菜大妈、快递小哥、建筑工人、家庭主妇……他们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、生活里的酸甜苦辣,还有对未来的向往,这些文字满是烟火气,最能引发大众的共鸣。我特别喜欢读他们的作品,比如陈慧的《在菜场,在人间》、王计兵的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,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正能量总能打动我。受这些作品启发,我也把身边看到的人和事写进小说,《焦虑》和《芦花飘飞》两个短篇,就试着从一个侧面,写下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。
古人说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未来的日子里,我知道,只有永葆一颗“文学”之心,坚持广泛阅读、不辍笔耕,才能积蓄足够的力量。我只愿在这条文学朝圣的道路上,能走得稳一点,走得远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