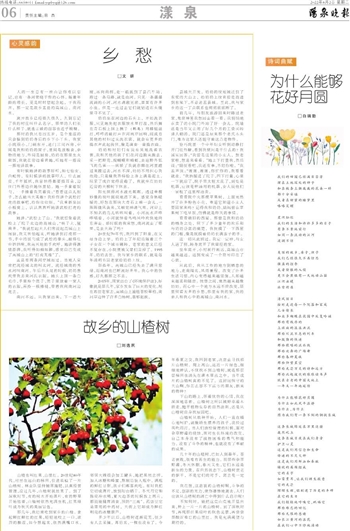人的一生总有一座山让你难以忘记,总有一条河萦绕于你的心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更是时时想起念起,于我而言,那一定是故乡盂县的高城山、南河水。
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很久,久到忘记了我的村庄叫什么名字,那里的人们长什么样子,就连亲戚的面容也近乎模糊。
那时的我只有四五岁,是个羞涩的只会躲到奶奶身后的乡下小丫头。我家小院很小,门朝东开,进门三间西房,中间是我和奶奶的屋子,里间是放粮食、杂物的地方,外间是厨房,奶奶在那里生火做饭,我就在旁边看着她,听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故事。
有时候她讲的故事好听,如七仙女、白蛇传,有时候讲的故事吓人,什么画皮、千年狐妖,我害怕得都要捂耳朵,边往门外看边往她怀里钻。她一手拿着饭勺,一手搂着我笑着说:“看看这点儿胆子,怎么能当大英雄?我给你讲个武松打虎的故事吧,给你壮壮胆。”我重新坐回小板凳上,认认真真听她讲武松打虎的故事。
她讲:“武松上了山。”我就想象着武松上了院子北边的高城山,“林子大,猛兽多。”我就想起大人们常说起高城山上闹狼,我又害怕起来,听她讲到打虎那一节,手中的饭勺成了武松的拳头,敲得灶台铛铛响,我高兴地拍手欢呼。她讲得激情澎湃,我听得如痴如醉,感觉自己变成了高城山上的“打虎英雄”了。
盂县有两条河穿城而过。当地人常常把流经城北的叫北河,流经城南的秀水河叫南河。午后日头足的时候,奶奶喜欢带我去南河洗衣服。她头上顶一条白毛巾,手里挎个篮子,篮子里放着一家人的衣服,再拎一根棒槌,带着我向南河边走去。
南河不远。从我家出来,下一道大坡,再向南拐,走一截就到了县汽车站,跨过一条马路,就是南河。只见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,河水清澈见底,里面有许多小鱼,但是一走过去它们就钻进石头缝里寻不见了。
奶奶坐在河边的石头上,开始洗衣服,只见她先把衣服放水里打湿,然后搁在青石板上抹上胰子(肥皂)用棒槌敲打,咚咚的敲打声在河两岸回响,间或有其他的村妇过来洗衣裳,就会有更多的捣衣声此起彼伏,像是演奏一章捣衣曲。
奶奶和村妇们有说有笑地洗着衣裳,我和其他的孩子们在河边跑来跑去,采一把野花,捉蝴蝶和蜻蜓,去追野外低飞的鸟雀……疯够了我就赤脚在河里蹚过来蹚过去,河水不深,奶奶不用担心我危险,只是嫌我弄得脸上身上满是泥土。玩累了或许觉得没趣了,我就坐在奶奶近旁的大柳树下休息。
阳光照得河水波光粼粼,透过垂柳妙曼的枝叶斑驳地洒下来,感觉身体暖暖的,好想在那块大青石上睡一会儿,一阵阵微风袭来,又顿觉神清气爽。河岸上不知名的鸟儿咕咕叫着,小河流水声哗哗唱着,小河就伴着鸟鸣风吟欢快地向东奔去。那时候的我常想,南河流去了哪里,是去大海了吗?
20世纪70年代,我回到了阳泉,在父母身边上学,奶奶上了年纪后随着三个子女在三个城市辗转,老家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,小院便被父辈们卖掉了。1995年,奶奶去世。我与家乡的联系,就是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给奶奶上坟。
那些年,高城山已经失去了满目葱绿,而南河也已断流好多年。我心中的伤感,好久都挥之不去。
2015年,国家出台了《环境保护法》,好像就是那几年,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现在再回老家去,高城山上遍植苍松翠柏,南河岸边种了许多白杨树,蓊郁挺拔。
县城大开发,奶奶的坟地被迁到了东梁的大山上,给奶奶上坟直接走高速到东梁下,不必进盂县城。至此,我与家乡的这一丁点联系也彻彻底底断了。
前几年,与朋友旅游回来时路过老家,鬼使神差我想回去看一看。我悄悄地在卖了的小院门外站了好一会儿。院墙还是当年父亲用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买砖请人砌的,院门还是原来那个老式木头门,难为这家人还能守着这点老物件。
恰巧院里一个中年妇女听到动静打开门往外瞭,看到我便问是干什么的?我诚实回答:“我曾是这里的小主人,想老家啦,想进来看看。”她上下打量我,然后说:“随便看吧,我还有事,不陪你啦。”我连声说:“谢谢、谢谢,你忙你的,我看看就走。”我抬腿进了院子,四下打量,心里一下就凉了,院子里太脏太乱了,到处是机器,应该是榨油用的机器,女人说他们一家租了这里榨油卖。
看看院中央那棵苹果树,上面竟然开了许多粉色小花,难道它知道小主人要回家来吗?记得我和奶奶、姑妈曾在苹果树下吃早饭,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。
看看破旧的西屋,那曾是我和奶奶的栖身之处,留下了多少童年的欢乐和与奶奶分离的痛楚,我抚摸了一下西屋的门框,像是抚摸着奶奶长满茧子的手。
这一切从此别过。我定一定神,与女人道了别,转身离开了我曾经的家。
坐车离开,小村渐行渐远,高城山亦越来越远,远到变成了一个符号印在了心底。
从此后,我从工作的地方到栖息的地方,走南闯北,风雨兼程。改变了许多生活习惯,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强,人却越来越柔和随意。恍惚之间,竟然越来越像奶奶。而心中一个地方永远不曾改变,那里留着太多的乡愁,那里有我的家、我的亲人和我心中的高城山、南河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