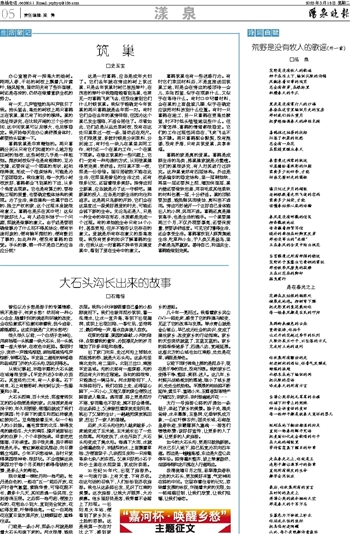曾经以为乡愁是游子的专属情感,我不是游子,何来乡愁?然而有一种心心念念,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改变,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牵着我,抚今追昔,感慨感叹。这或许就是广义的乡愁吧!
很久很久以前,一个白胡子老神仙,用麻秸棍一头挑着一块大石头,另一头挑着一座大铁钟,在夜色中赶路。黎明时分,突然一声雄鸡报晓,麻秸棍被鸡鸣声惊断,钟落石坠。平定县二道街的钟楼巷和县城西门外的大石头沟,因此而得名。
从我记事起,半隐半露的大石头就在城墙根安卧。《平定州志》中称为茄石。其直径约三米,有一人多高。石下有泉,石上有酸枣树、枸杞树以及一些藤蔓和小草。
大石头西南,百十米处,那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便是我的家。北房原来是有房子的,年久而损毁,倒塌后就成了我们的菜园:竹子架下的黄瓜和西红柿像是红颜知己。豆角缠绕着玉米,似一个粘人的小姑娘。毫毛茸茸的北瓜、绿得发亮的嫩倭瓜、大大的南瓜、撑开地面钻出来的白萝卜,个个丰腴饱满。洋姜疙疙瘩瘩,子孙满堂。茄子很光滑,茄子蒂却很是扎手。青红辣椒迎风摆动,向日葵鹤立鸡群。少年不识愁滋味,当时只觉得菜园很神奇、很好玩。不会理解这块菜园对于每个月买粮时都得借钱的光景,是多么大的帮助。
院中栽着一棵牡丹和一池芍药。牡丹是白色的,一般在“五一”前后开放,花开时香气氤氲,素雅华贵,可惜花期不长,最多十几天,其间若遇一场风雨,立刻香消玉殒。之后那一池芍药,便接力似的,花苞由小到大,直到完全绽放,花红得发紫,叶绿得油亮。一红一白两池花在夏日里次第开放,让蝴蝶留恋,蜜蜂往返。
门前是一条小河,那条小河就是顺着大石头沟流下来的。河水很清,能洗衣服。我和小伙伴曾跟着自己叠的小船顺流而下。我们也曾用泥沙筑坝,蓄一泓清水,让水一直升高,等坝下出现漏洞,或坝上出现凹陷,一番忙乱,坚持再三,最后哗啦一声,看水自奔流人自欢。
花草的惊喜、菜园的奉献、小河的陪伴,点缀着我的童年,为捉襟见肘的岁月增加了许多丰稔和浪漫。
出了家门向东,走过河沟上预制水泥板搭的桥,就是大石头沟。这条沟呈南北走向,有二里许。北到三岔口,南接平定县城。沟的北部有一座煤窑,沟的西边有大片的庄稼地。当初的路很窄,只能通过一辆马车。河水顺势而下,人车择路而行。我们在路上走,还得留心脚下,一不小心,又暄又厚的煤尘便没过脚面进入鞋里。遇雨雪,路上更是泥泞不堪,穿雨鞋也不好走,搞不好会滑倒。在这条路上,父亲曾担着煤炭走到阳泉,挑出了父辈的生计;一趟趟把煤炭挑回家,担出了一家人的温暖。
后来,大石头沟住的人越来越多,小麦地变成了玉米地,玉米地长出了一处处院落。河沟变浅了,水也污染了,大石头沟变成了臭水沟。每遇下大雨,水就会倒灌进院子,半腿深的水,上面飘着草秸、方便面袋子、几块西瓜皮和一只凉鞋等杂七杂八的东西。父亲只好把小石子和沙土装在水泥袋里,筑成防洪堤。 20世纪90年代,出现了旅游热。有一句流行语: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。在这句话的召唤下,人们纷纷到苏杭旅游。我也从这条路出发,见识了江南的美景。这次旅游,让我大开眼界,大为羡慕。他乡虽好终是客,我带着不舍踏上了归程。一出阳泉火车站,便看到了家乡灰头土脸的容颜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对比之下,感到家乡的差距。
几十年一晃而过。我看着家乡风尘仆仆一路走来,感受了它的阵痛与蜕变,见证了它的改革与发展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,变成了建设家乡、改变家乡的行动指南。家乡的天空突然就蓝了,瓦蓝瓦蓝的。家乡的路渐渐地多了,四通八达,宽阔延展。这座北方的山城也如江南般,处处是花草,满眼是绿色。
以前下雨时裤角上溅的是泥点子,现在是干净的雨水,没有污痕。我的家乡已变得干净、整洁、美丽、迷人。这几年,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落地,缩小了城乡差别,处处生机勃勃。平展展的柏油路不断延伸;黄瓜干、富硒小米、玉露香梨等特产行销四方;农家乐、农村游遍地开花……
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开通如一条链子,串起了家乡的美景。娘子关,雄关耸峙,水丰瀑激;玉皇洞,亿载钟乳成万象,一山红叶醉古州;固关长城,石砌故垒春秋迹,京畿藩屏九塞魂……游客们啧啧称赞:该好好宣传,让更多的人了解,让更多的人来旅游。
如今的大石头沟,更是旧貌换新颜。河水已引入地下,路已拓宽为双向四车道。西边是一幢幢高楼,东边是大型公共停车场。路旁灌木整齐,坡上绿意盎然,法国梧桐和龙爪槐在人行道两边。
汲清流增日月之恒,添翠微染春秋之色的大石头,更加美好丰富,气定神闲在路的中间。它留存着往昔的记忆,容纳着发展的咏叹,怀揣着未来的无限,如一部鸿篇巨制,让我们欣赏,让我们咀嚼,让我们眷恋。